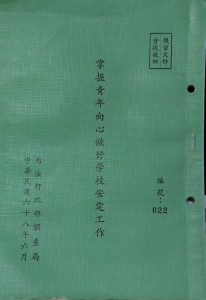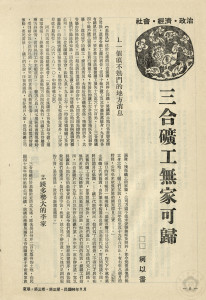採訪側記,及反思如何採訪與理解「白色恐怖」政治案
♦ 文、圖/張立本
去年某本「白色恐怖」相關著作,從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一刀為二,以此判定鬥爭的差異;此異論即使承認六○年代以後在美、日帝國主義加持下形勢轉變,但從「方法」看,就只是將事件依序排,從而只能把反覆出現的、有具體意識形態的「左派」群體視為偶然,甚至多元文化的一環,反而無法反映長時期的社會歷史動態。
黨國: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
我尋著前人們「買書」的路徑,又在舊書攤找到一份一九七九年「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號022號的機密文件<掌握青年心向做好學校安定工作>,從中可見,即使「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青年被逮,黨國仍然關心您。
當局始終擔憂「共匪」滲透校園利用「純潔青年好奇之特性」;當局認為,鄉土文學、海外台獨與島內台獨宗教勢力、受「匪」影響之歸國學人等,都是「敵人多方衝擊」之表現;故應「提高大專青年政治認識、了解民主自由之真諦」。顯然,黨國及其餵養的人們並不知道自己面對著什麼。社會變遷過程產生社會矛盾,只要稍為不滿於僅僅「自我成就、自我完成」,則必然去接觸且探索源由、對社會苦難的人們產生感同。
青年:哪兒有壓迫我就去哪兒!
但這給了我們第一條線索,先看淡江大學「時事研習社」。蔡裕榮一九七四年入學時,「時研社」只剩下宋東文一個人。「為什麼參加?因為他招生時的看板,貼著『阿拉法特』照片,身上披著一排子彈,手上拿著機關槍,感覺很酷。」蔡裕榮說。
蔡裕榮記得,「在那兒聽宋東文談『巴勒斯坦』問題,覺得很有意思。知道有以色列,卻從沒想過阿拉伯世界的問題。而且,好像終於可以拋開長期不懂裝懂的『存在主義』時期。」他且說「直到現在,只要有人發起抗議以色列的『站樁』就一定去。人家問,六十歲的人了為何還去靜默抗議?只能說我思想上的啟蒙是從這裡開始,而且這是人類世界正義的問題。」
當時大學校園常有「服務隊」,今天也延續。宋東文、蔡裕榮們也參與,去山地偏鄉,去農、漁村,去礦村,跑遍台灣。今日許多青年或與當時青年一樣,覺得關心窮困地區、老人、小孩,很能展現愛心。但蔡裕榮回憶到,「有時私下嘲笑這是戀愛隊,上山帶小朋友,然後談戀愛。」他說,「總覺得大學生不該有高貴心態,如果只是幫忙農民收割、陪小孩玩遊戲,卻沒有趁機跟農民多聊、理解農民困境的社會根源,或沒能在參訪部落時,從原住民口中理解原民社會的文化,那就很可惜。」
宋東文更直說「社團本身做不了什麼事情,只是讀書會、請校外人士座談。」但慢慢的,讀了「馬、列思想」以後,他說「幹部訓練時就會想藉由相互批評來提升彼此的水準。」但那時代,宋東文直言,即使「覺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社會,感覺熱血沸騰想貢獻自己的力量,可是很難,因為我們憑書中的描述,自己想像革命是什麼樣子」;蔡裕榮也說,「講實在話,當時大家年紀輕,也找不到真正的方向跟出路,回想起來只是一些嘗試」。不過,單憑此想像,宋東文們不僅去偏鄉,「也想滲透、掌握別的社團,從中找到適當的人,擴大自己的同伴」。
左傾學生運動:組織學工,碰撞出路
。-205x300.jpg) 在大學錄取率僅「26.83」的1974年,大學生還能如何?根據蔡裕榮,在仍屬「經濟奇蹟」的日子裡,無論文科、理科學生都有理由相當自信,不會對未來有惶恐。但是,蔡裕榮說「除了課業以外就是參與文康活動。因為長期政治恐懼,也很自然避開政治」。
在大學錄取率僅「26.83」的1974年,大學生還能如何?根據蔡裕榮,在仍屬「經濟奇蹟」的日子裡,無論文科、理科學生都有理由相當自信,不會對未來有惶恐。但是,蔡裕榮說「除了課業以外就是參與文康活動。因為長期政治恐懼,也很自然避開政治」。
即使整體經濟在上升,並非所有人都無虞,「私立大學學費高,對某些家庭負擔不小,」蔡裕榮提及,若是大學生,大部分人會選擇當家教,外面的工作機會條件卻很差;於是「時研社」將眼光放到工讀生身上,想「成立工讀生聯誼會,把家境比較窮的人整合起來,幫忙找工作,以及薪資集體議價,或者在校內找機會、找獎學金,針對各方面做服務。」
這可能是戰後台灣最早的大學生自發勞動權益團體,即使未竟。蔡裕榮記得,「課外組組長說不准」,理由為何?他站在組長面前等解釋,「組長邊想理由、邊在紙上塗鴉,塗著塗…在紙上反覆寫『工讀生聯誼會』、工讀生聯誼會…最後他自己把「工讀生聯誼會」縮寫成『工會』」,然後就想到理由說「不可以組工會!」
「時研社」是課外組的眼中釘,成員們亦自知。但回憶時更感嘆「在整個社會上也找不到有力的團體或組織,沒有主導性的力量」,老政治犯都是耳聞,早幾年「成大共產黨案」中的淡江成員也只是學長口中的話題罷了,實踐方法只是闖路。或許在當局眼中只是大學生活動,或由於未有成效,或由於成員篩選嚴,雖常被校方阻礙,但沒出大事。可是,實踐與思想的辯證,或許仍埋下了更強組織化的引信。
藕連:文藝青年看電影聽音樂
往前倒敘,把時間拉前,賴明烈於一九七○年入學「文化學院」。賴明烈不記得過程了,卻記得甫北上便省吃儉用,去牯嶺街補齊了高中就經同學介紹閱讀的《文星》雜誌,且狂覽寫實小說。他特別記得,黃春明書寫的宜蘭農村經驗讓他頗能同理,但「像〈蘋果的滋味〉那種描述外商嘴臉的小說,應該也起了一定思想激化作用」。
賴明烈在台北大量接收電影、文學、音樂,且是「聆音社」社長。因在學校社團活動認識了戴國光、劉國基,又聊得來,視聽覺開始出現戴、劉介紹的「反戰音樂」、「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等左傾文藝,並且有意識地以「聆音社」為平台推廣「反戰音樂」。賴明烈高中畢業是一九六九年,世界性學生浪潮的時代,聽點「Joan Baez」的音樂似乎頗正常;但賴明烈常讀的《影響》雜誌等,卻透露著一九六○年代更早一批台灣青年文藝的活動遺產,起碼如《劇場》、《文學季刊》。
賴明烈說,戴國光喜歡聽音樂,身邊也聚集一批私下看實驗電影的朋友;戴華光也說入獄前受弟弟影響聽反戰音樂。文化法文系轉學輔大的劉國基呢?由於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的緣故,又由於「不想讓校刊只是校內學生的作文簿」,故認識了大量文友。據劉國基說,因為邀稿而認識了「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成員。正如牯嶺街之於賴明烈,劉國基也透過中一中旁的「美國新聞處」、台中公園旁舊書攤,嚼食禁書,或讀著美國人家裡流往舊書攤的各種美國雜誌。美新處的材料或許經過「文化冷戰」的篩選,但仍讓讀者填回台灣報紙上被剪去的新聞。
舊書攤老闆丁穎後來開了「藍燈出版社」,期間劉國基因在「藍燈」打工而常隨丁穎去「中一中」訓導處一位組長家裡,在組長兒子李敖的書櫃中翻找材料印行台灣版。一九七二年高中畢業,劉國基也通過丁穎認識書友王曉波,從而開啟了一段台北時期的友誼。
鄉土:必然發生的偶然
除「時研社」捲進「上山下鄉」風潮,我們尚未提到,賴明烈當兵時,某次北上寄宿好友戴國光家中,戴國光同樣細數著參訪雲林、台西偏鄉的震撼。賴明烈說,「戴國光見到那邊村子的貧困,而我小時候在嘉義鄉下農家,農忙時期就是請這些地區的人來幫忙。比較窮的農民,自己的工作做完了,或者自己沒有田,就從南部依著收成先後一路北上打工。所以我聽他講時也很激動」,兩樣經驗說到了一塊兒。
七七年九月,《夏潮雜誌》刊出署名「柯以書」的文章。賴明烈解釋這個筆名,「『柯以書』的意思是『可以書寫』,因為我覺得,雖然戒嚴時代管制很嚴,但這種事情應該還可以寫吧?賴明烈怕我不懂,說「這是列寧說的,必須一個個實地調查,才能知道剝削的鎖鏈是怎麼連結起來的……」。這比一般熟知的八〇年代中期「杜邦」學生調查整整早了十年。
〈三合礦工無家可歸〉的詳實分析,與《夏潮》編委全然無關;因青年們共同經驗的前提,及「社會情況就是如此」之故,才使得相遇並結成組織後,累積集體經驗並形成報導。回想我前文摘錄的「機密文件」,當局顯然不理解,從而只能一再織成「為匪利用」;但青年行動恰恰反映了台灣的社會狀況,更反映出當局早已為時代所限、被拋出了歷史的事實。
不可思議的思想喜悅
從青年問題談到這兒,讀書,文藝,社團組織,熱血澎湃勇於試驗。關鍵在於,活動與思想變化全都發生在一九七七年底案發前數年,有人在當兵,有些人不認識,「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沒影子,當然也沒有「青年涉世未深受蠱惑」這事兒。劉國基反覆強調此點,說「我們案子兩個特點,一,和中國共產黨沒有『組織上的』關係,二,所有的人都是台灣出生、台灣長大。」這大概也是蔣經國疑惑之處。
「賣書」是戴華光歸台以後的事;零零總總、程度不一地影響著青年思想的「書」,在調查局眼中是「不法意圖」的掩飾或「物證」,但賴明烈回想起來,「因為覺得這些書很好,感覺賣這些東西就是自己在傳播好思想」。賴明烈當時已有工地監工的好薪水,卻「請工地工人幫忙釘製木箱,每個禮拜騎摩托車載去師大、台大附近賣。」當世界觀轉變,世界顛倒回來。賴明烈憶及,「確實沒想過賣書的危險性,但當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心情,無怨無悔。只覺得,如果生活真能跟理想結合,那是多麼美妙?回想起來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在賴、劉與戴華光更深交往前,或許劉國基也恰是因為很難說清楚的「思想的喜悅」,介紹賴明烈從「無政府主義」一路讀往「科學的社會主義」。
不似「個人主義」,以上不是凸顯單個英雄多麼思想深刻或實踐激烈;即使每個人確實有自己的特殊啟蒙路徑,也難精確回溯斷裂性思想豹變。青年們都一樣,在不可能有明確「左」的思想指導的社會環境裡,只能自行在各派世界觀、真真假假的思想介紹中摸索,從而也不可能指出單個人佔據思想指導高位。「案發」太快,活動迅速中斷,也不可能歷史重來、檢驗上述行動可行否。然而故事輪廓很明晰,他們都在台灣本地社會的土壤裡,汲取著任何的可能性。
但「本地土壤」意味著什麼?當然了,若沒有「保釣」傳承「文革」的上山下鄉,台灣當局恐怕不會試圖以「救國團」活動轉移青年注意力,卻間接保下思想震動的契機。但再把視線拉前,若非匯聚在《夏潮雜誌》的、如蘇慶黎、陳映真們之推動,若無五○年代政治犯陳明忠的第一筆資金,則判決書中所謂戴華光們「販售合法書刊」之一的《夏潮雜誌》,也是叛逆青年宋東文認為在「上大學後產生知識上的轉變、逐漸左傾」過程中「徹底改變」他思想的關鍵之一的《夏潮雜誌》,恐怕未必出現。「土壤」誠然受限──別忘了,陳明忠捐款隔天即「二進宮」──但它確實有作用。這提醒我們,仍須適當的方法才能看見事件順序下的真實內容,也提醒了如果行動不可能有未來,同樣得在長期噤默的白色社會尋找答案。
國際:華埠「反蔣」與「重新認識中國」
到這兒還沒提到戴華光。戴華光又怎麼呢?跑船時到了越戰發生地,到了東南亞的華阜,到了仁川,看見什麼?想著什麼?在宋東文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我們前往河北滄州見到了戴華光,這趟旅程對「理解『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幫助是什麼?下回見曉。(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