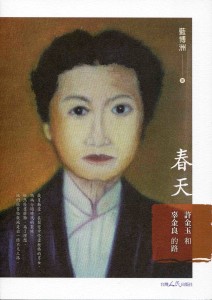文/蕭毅
革命,在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日益遙不可及,而革命往事的重溫則於新的反抗不無意義。在宏大的時代洪流中,既有正面迎戰的政治精英,也有投身理論的左翼文人,還有名不見經傳的參與者。《春天》所向我們講述的,正是兩個革命參與者的故事。他們雖普普通通,然而由其一生的努力卻不難洞見革命的偉岸與艱辛。
辜金良,1915年出生於嘉義,父親是一個雜貨店商店。許金玉,1921年出生於台北,生父家貧窮,而養父則是小有所成的包工頭。兩個人的家庭出身,雖然談不上富庶,倒也殷實,以至於許金玉喝牛奶的習慣一隻保持到九歲。那麼,他們又是如何走上革命者的道路呢?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台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島上的反日運動和農民運動風起雲湧,辜金良與許金玉因此也經歷著民族與階級意識的雙重啟蒙。辜金良的民族意識萌芽於小時後去媽祖廟裡聽各種抗日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則是墓碑上的「土匪」實際上卻是抗日義軍。在公學校四年級,他因為批評老師是「日本走狗」而被毒打。許金玉的民族意識則萌芽於受益於養父。無獨有偶的是,文化協會在各地的演講也都成為二人觀念的啟蒙者。一個從嘉義的農地,另一個從龍泉汽水廠,目睹壓迫與剝削,意識到勞動者的悲慘處境。這一民族與階級意識雙重啟蒙下的價值立場成為影響他們一生的生命底色:與八路軍聯繫、投入工人運動、被捕入獄、誠實經驗皮蛋行業、支持祖國統一。
然而,革命卻是艱辛的。它要面對的是形形色色的敵人,是以陣營的內部也呈現出一種駁雜:其中,既有如計梅真、錢靜芝、林堂欽之類的不屈者、慷慨赴死,也有敵人安插的各種內線。獄中,辜金良等人藉著葉青的反共書籍而學習其中的共產主義引文,有人疏忽沒有抄寫批判性的文字而被揭發,結果導致三十多人被槍決。敵人,不僅是有形的,更有可能是無形的:有些人因為長期沒有家人的接濟,因而在吃的上頭跟人起爭執;也有些人在獄中慢慢不再談論共產主義;還有些人則因為不同的策略而分派。
二十世紀台灣左翼的歷史實踐,載浮載沉,充滿悲壯。五零年代初的白色恐怖,造成大批共產黨人罹難。黨人的付出雖未撼動舊統治的基礎,先賢翹首以盼的祖國統一作為敏感的政治禁忌在島內依然存在,然而革命之於女性的雙重改造意涵卻不宜被忽視。女性在參與社會改造的同時,也完成著自身的改造。許金玉養母對其教育,完全遵循封建禮教,要求女孩子即使笑的時候也不能出聲。再加上日本公學校的教育強調服從,導致她比較害羞,看人的時候不敢正視。然而,在計梅真的鼓勵下,許金玉勇敢地邁出了第一步:她會前積極收集同事的意見,郵政局工會代表大會上大膽發言,甚至一躍而為工會的活躍分子。這讓其舊識蔡茂桂大為吃驚。在隨後的社會活動中,許金玉積極參與,從而完成了自我的改造,從一個受封建禮教與公學校教育束縛的女性,成為獨立自主、敢於表達和追求自我權益的現代女性。
在坎坷不平的生命經驗中,辜金良和許金玉雖然歷經千難萬險,卻是九死未悔。直至生命的晚年,許金玉依然認為「我們過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沒有關係,只要大家能夠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之於理想,他們始終懷抱著一份忠貞。在獄中,沒有出賣同志。出獄後一段時間,兩人努力經營皮蛋事業,科學管理,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企業即使沒有剝削,也可以獲利。儘管事業取得很大的成功,然而他們卻選擇省吃儉用,把錢捐給為了社會公平與祖國統一而努力的團體和個人。更為可貴的是他們的清醒。辜金良年輕的時候,受到楊逵的影響,曾經有寫作的夢想,後來意識到做生意可能更是自己的內行。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在革命事業中所要扮演的角色。這樣的自覺,也使得他們在後來的生活中保持了足夠的韌性。在左翼的前輩中,他們並非理論家,也不是身處核心的組織者,而是參與者。正是這樣一份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默默付出,使他們贏得了人們的尊重。
回到這本書的最後,藍博洲先生道出其良苦用心。他希望包括那些沒有到過台灣的大陸同胞知道,除了少數為非作歹的「台灣歹狗」,還有很多像辜金良先生和許金玉女士這樣善良的台灣人。這樣的一份心意,在兩岸關係轉冷的今天,也格外溫暖。期許更多的朋友能夠讀到《春天》,也能夠記得曾經有這樣兩個老人:樸素、堅韌、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