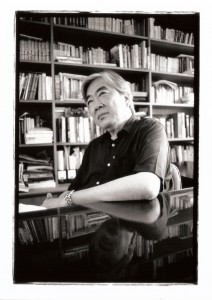♦文/路況 (成功大學副教授)
我不認識陳映真先先,記憶中唯一一次接觸是多年前在一家文學雜誌任編輯,曾透過電話向陳先生約稿。我想記述的,是站在一個純粹讀者的立場,從年輕時的隔閡不解,多年以後因為個人際遇而遲來的左翼思想啟蒙,對陳映真因為在台灣堅持左翼左統立場而不被理解乃至飽受誤解敵視,汙衊排斥,陷於一種「沒有位置」的「異端」、「異教」位置的尷尬弔詭困境,逐漸產生更多的理解體會,以末學後進的「後見之明」向一位「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的先知先鋒表達一點遲來的敬意與感佩。
八〇年代初期,我高中念建中夜間部,對文藝有興趣,讀了不少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與遠景出版社的書。記得有一晚九點多下了課,急急走到建中對面的植物園禮堂去趕一場名作家座談會的結尾,大概是中國時報主辦的,那晚出席的有司馬中原,白先勇與陳映真,的確是那個時代台灣文壇的三個文星級偶像作家,可分別代表戰後台灣小說的三大流派:司馬是軍中作家的代表,白是學院派《現代文學》作家的代表,陳是《文季》派小鎮知識分子作家的代表(一如七等生與黃春明,陳先生當時出獄不久,在一般讀者眼中,頂多是反國民黨的異議分子,左翼立場還隱而未顯,更別說左統。)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對司馬中原與白先勇算相當熟悉,對陳映真雖也讀過不少,卻頗為隔閡不解,甚至有種莫名的反感。箇中理由不難理解,我是家在台北,成長於國民黨戒嚴教育體制的五字頭一代,國父、蔣公的三民主義民國革命法統以及孔孟四書的中國文化道統是構成中國意識形態世界座標的X軸與Y軸,日常娛樂則是老三台電視連續劇,國片、港片,美國電影、電視影集及流行樂排行榜,少棒青棒賽,男籃女籃賽和瓊斯杯籃球賽,在這一整套體系中幾乎沒有陳映真的位置。(勉強可找到兩項:一是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創造了「上班族」這個流行語,預示了當時方興未艾的都會中產階級小資情調。另一項是在電視上看到重播舊國片《再見阿郎》,白景瑞導演,柯俊雄主演,後來才知是改編自〈將軍族〉。但使這部電影成為「國片經典」的其實是柯俊雄最拿手的吃軟飯小白臉的經典演出,與〈將軍族〉原作幾乎扯不上關係。)
如以中國古典文學類比,如果說白先勇似《紅樓夢》,司馬中原似《水滸傳》,那陳映真簡直遙遠陌生如《水滸傳》裡的方臘,是中國文化正統儒家道統眼中的「異端」與「邪教」(所謂「馬列邪說」),根本容不下或刻意視而不見,如明教、白蓮教或太平天國。(蔣介石反共打出的旗號之一就是自比為曾國藩,而將中共類比為背叛儒家道統的太平天國。中共似乎也認可了此一歷史類比,所以一度將京戲《鐵公雞》列為禁戲。)
趙剛說陳映真是台灣作家中唯一繼承了五四魯迅一脈的左翼書寫系譜,我認為說對了一半。因為魯迅畢竟還是中國文人士大夫傳統教育薰習出來的,儘管反孔反儒反士大夫,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但舊派文人氣的脾性毛病可一樣也沒少,和胡適、陳獨秀一樣都好寫舊體詩一吐胸中鬱壘牢騷。其實從前五四的康有為、梁啟超到五四末期的毛澤東皆然。可是在陳映真身上卻幾乎看不到一絲中國舊文人氣,倒是有一種殊異東洋味的異國情調頹靡氛圍。前幾年讀到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舊譯《三十三年落花夢》較有味),宮崎自敘其追隨孫中山投身中國革命生涯的烈士情操與浪人頹放,發覺與陳的東洋味頗有神韻相似處。
我大學唸政大哲學系,大四時考上台大哲學研究所碩士班,正值台灣解嚴前夕,台大、政大附近常見幾台小卡車停在路邊販售大陸簡體版書。我還買了不少雙葉書店的英文盜版書,多是介紹歐陸思潮的存在主義、現象學、詮釋學、批判理論與解構主義,更多則是從台大圖書館借英文原版書直接拿去影印。我從那時開始嘗試援引套用法國德國前衛理論的概念架構來分析批判解嚴時代台灣社會政治的各種亂象怪兆,寫了不少所謂的「文化評論」投稿當時的《南方》、《當代》、《中國論壇》與《自立早報》副刊。我記得還趕上《文星》雜誌復刊號的倒數第二期,發表了一篇論後現代主義的萬言長文,後來《文星》就停辦了,稿費也沒拿到。大概是研二時認識了王浩威、李尚仁、吳昌杰、楊明敏、蔡榮裕、吳正桓、陳光興、蔡其達等朋友,每周在浩威家辦讀書會,讀法國前衛理論(拉岡、傅柯、德勒茲等),當然是透過英譯本一知半解地苦讀。那時正值陳先先創辦《人間》雜誌,記得有一次鍾喬以《人間》記者的身分來參加讀書會,當然已忘了講了些什麼。現在回想起來,陳先生當年搞讀書會的代價是被警總約談和送去唱綠島小夜曲,相形之下,那時的我們可以在解嚴年代自由無懼的搞讀書會,真的是台灣的思想啟蒙時代最幸福的一群閱讀公眾(reading public),可惜那時的我們真箇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