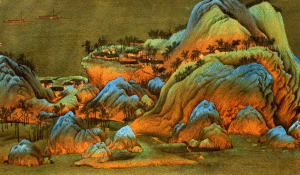王希孟,一位在畫史文獻中沒有任何記載的北宋宮廷畫家,一位身世撲朔迷離的山水畫家。他18歲時,竟然僅用半年時間便繪就了《千里江山圖》,這既是他唯一的傳世作品,也是存世青綠山水畫中最具代表性和里程碑意義的作品。
2007年9月15日起,這幅11.9公尺長的經典青綠山水畫作,罕見地全卷打開,亮相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
聽得到的青山綠水
從全卷的構思構圖來看,整幅圖卷就像一首波瀾壯闊的古典樂曲,形成了亢奮而優雅的旋律,節奏感十分鮮明。全圖由七組群山組成,因而可以分成七個自然段,彷彿就是七個樂章。
開首第一組群山為序曲,較為平緩的山峰在俯視的地平線下,漸漸將觀者帶入佳境。第一組和第二組之間以小橋相接。第二組就像是樂章裡的慢板,又如一曲牧歌,悠揚舒緩。第三組和第四組之間以長橋相連,環環相扣。
進入第三段、第四段,山峰一個個衝出了畫中的地平線,走向高潮。在鐘鼓齊鳴中,最高的主峰在第五組輝煌出現,她如同廬山中的漢陽峰,拔地而起,雄視寰宇,形成了樂曲的焦點,她與周圍的群山形成了君臣般的關係,構成全卷的高潮。
第六段,群峰漸漸舒緩下來,遠山慢慢地隱入遠方大江大海的上空,欣賞者激動的內心漸漸平靜了下來。最後一組如同樂章中的尾聲,再次振奮起人們的精神,畫家用大青大綠塗抹出近處最後的幾座山峰,如同打擊樂最後敲擊出清脆而洪亮的聲響,在全卷結束時,回聲悠遠,令人難忘。
圖中的大山大嶺屹立在江湖沼澤之畔,在北宋統轄的疆域裡,只有江西廬山有此特性。畫中展現了開闊的水域,近處水草叢生,遠處煙波浩渺,像是長條形的沼澤大湖,遠接江海,極似鄱陽湖一帶的濕地、沼澤。畫中的建築樣式、竹林,廣泛使用的竹籬笆、竹篙、蓑衣、笠帽等竹製品,還有腳踏式雙體船、挖河泥的勞作等,表明所畫地域為江南湖區。特別是畫中兩次出現疑是祭祀匡神的穹隆草廬。廬山最著名的三疊瀑被改為四疊瀑等,其基本形態與廬山十分相近。因此,畫家畫的主景是廬山和鄱陽湖。
《千里江山圖》卷描繪了整個廬山大境,還包括長江口和部分鄱陽湖,全卷充滿了詩意。查遍北宋以前吟廬山的詩詞,與《千里江山圖》最接近的是唐代孟浩然的五言詩《彭蠡湖中望廬山》(鄱陽湖古稱「彭蠡湖」)。
王希孟並非簡單地圖解孟詩,圖中所繪時節極為細膩,孟詩中的一些基本元素幾乎都可以在圖中一一找到。宋代日趨發達的商業經濟促使人們的生活節奏日益加快,形成了早起早行的風氣,甚至五更出行已成習俗。畫中的人們在清晨便開始忙碌了,有的船已經揚起席帆,還有灑掃庭除的童子、駕舟趕船的乘客、下山趕集的樵夫、上山遠行的馱隊等,而早起的隱士們則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悠閒姿態。
用生命換來的傳世名作
《千里江山圖》卷承載的是宋徽宗極力推崇的「豐亨豫大」的繪畫審美觀,因而必須將之置於北宋的繪畫審美意識的大格局裡,並且與其他不同的審美觀進行比較,才能深入領會畫中的意蘊。
從五代到徽宗朝初的宮廷畫壇,已基本形成了「悲天憫人」和「蕭條淡泊」兩種繪畫美學形態,前者是表現社會底層辛勤勞作的場景,後者是抒發文人畫家的灑脫或失落的胸臆。
「豐亨豫大」審美觀承接了北宋中後期技法求真、求精、求細和畫面求大、求全、求多的趨向,設色富麗堂皇。在宮殿內牆上壁畫、大軸以及屏風畫的色彩要富麗堂皇,這正是徽宗要積極倡導的審美觀。而那些具有「蕭條淡泊」和「悲天憫人」意境的繪畫是不太適合這裡的宮牆。
王希孟的艷麗醇厚的大青綠山水,完美體現了徽宗「豐亨豫大」的審美觀。徽宗十分關注宮中設色繪畫的發展,鼓勵用大青綠作山水畫是其一生中十分重要的藝術突破。在他登基之前,唐代大小李將軍的設色山水在北宋漸漸「褪色」了,唯有少數的宗室和貴胄畫類似小青綠的山水畫。而徽宗本人,除了個別的水墨畫之外,畫跡和代筆之作多數是用重色,十分鮮亮明麗。
徽宗「誨諭」王希孟畫《千里江山圖》卷,是為了提振青綠山水、特別是要開創大青綠山水的繪畫語言。王希孟除了在畫學受到過基本訓練之外,幾乎是一張白紙,極易領會並實現徽宗的意圖。當時的李唐、朱銳等人的手法已經定型,重塑的難度比較大。王希孟敢於大量使用石青石綠,這在以往是極為少見的,相信這是他的觀山所得:蒼翠蔥鬱之山,近則呈綠,遠則顯青,原因是空氣的厚度改變了遠處山林的本色。畫家繼承前人用色之法,概括提煉出青綠二色。
《千里江山圖》卷呈現出與「悲天憫人」和「蕭條淡泊」不同的繪畫面貌。它的出現並非偶然,與其他畫家的趨同性共同交織成宮廷繪畫的審美趣味,這也是山水畫發展從表現單體到連續性整體的規律所致。
再説希孟本人,為了實現徽宗「豐亨豫大」的審美觀,王希孟付出的是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王希孟這位天才少年,活在人世間才20年。他以涅槃換來了這件舉世名作,在他之後,幾乎沒有一件青綠山水畫的氣勢和境界達到如此不凡的氣度和高度。它是真正的大青綠山水畫,是中國古代山水畫史上一個新的開端。它在畫壇叫響了近兩個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