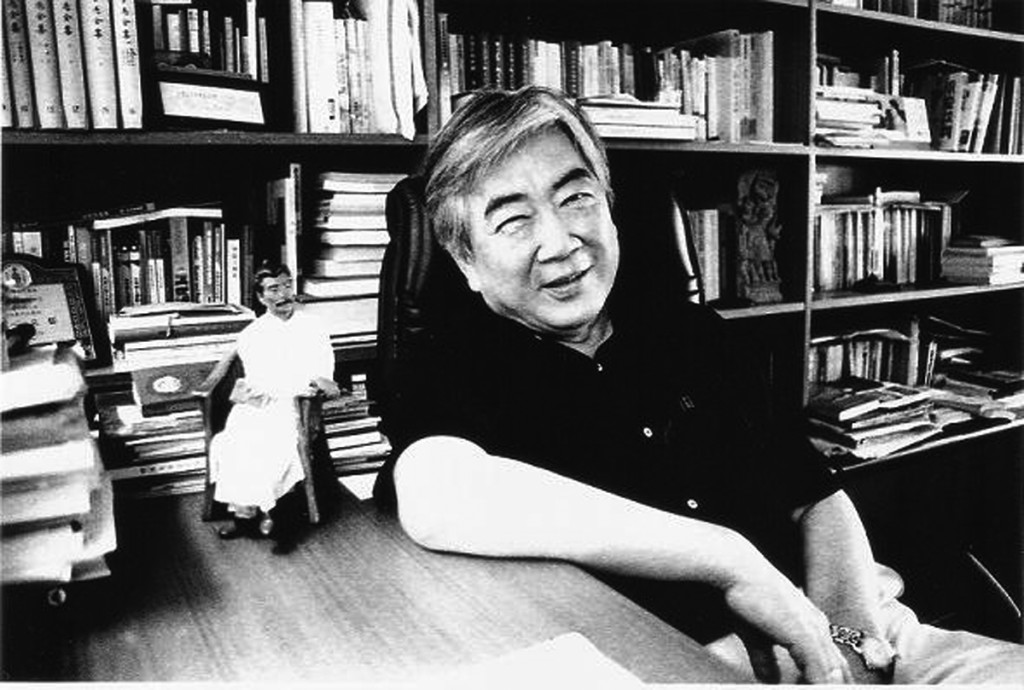♦文╱張立本
革命徬徨:「不完全改革」的空想調
深讀吳錦翔的「冒瀆地笑」、他的「悲哀」、他感受的「滑稽」,須回到至為關鍵的「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再展開。騷動與動亂,誠然觸動吳錦翔知識上的現實化,但也勾動了他的徬徨。
「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延伸到山村裡來以後,吳錦翔在內裡的混亂和朦朧的感覺中,不僅確認了自己之為這樣一個有著愚而不安的本質的中國人的不可說明的親切感,但「這樣的感情除了血緣的親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而曖昧的悲哀了」,他感嘆:
這是一個悲哀,雖其是矇矓而曖昧的──中國式的——悲哀,然而始終是一個悲哀的;因為他的知識變成了一種藝術,他的思索變成了一種美學,他的社會主義變成了文學,而他的愛國情熱,卻只不過是一種家族的、(中國式的!)血緣的感情罷了。
若將吳錦翔視為陳映真,則上述引文就會是陳映真自敘白色恐怖下的受壓抑情況。然若我們硬是將這段拗口文句照著文本走,它可以是思想震盪之後的自我反省,小說家通過吳錦翔的悲嘆,進而質疑:過去怎麼就沒因為「讀書」而真切體認,不可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改革、好轉」?那麼,另一段敘事也就不是陳映真的自我描述,而是迂迴提出批評:
幼稚病!他無聲地喊著。這個喊聲有些激怒了自己,他就笑了起來:幼稚病!啊,幼稚病!有什麼要緊呢?甚至「幼稚病」,在他,是有著極醇厚的文學意味的。他的懶、他的對於母親的依賴、他的空想的性格、改革的熱情,對於他只不過是他的夢中的英雄主義的一部份罷了。想著想著,吳錦翔無助地頹然了。
換句話說,陳映真通過吳錦翔的個人自諷,實際上嘲弄了吳錦翔剛回來山村時樂觀、熱情的、不徹底的空想改革論。不完全的改革論,是無稽的幼稚病:他的知識竟然其實是藝術,他的思索不過是美學,而他的社會主義僅僅是文學,他的家族熱只是血緣感情。
吳錦翔感覺徬徨。走到自我質疑這一步,情熱與樂觀已經不見了。調整思想後,誠然更近現實,但也由於才剛剛確認「愚而不安」的中國的現實改造問題,使得徬徨之中帶著矛盾。
吳錦翔調整思想,意味著必須構思新的實踐,故他「竟覺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瀆地笑出聲音來了」,發現自己早先廉價的空想改革論的可笑。但是面對現實的與自我的調整,還意味著另一個更大的困難,即吳錦翔面臨著調整認知、調整實踐方式之後的,未必能夠料想的新一輪後果。於是,1949年的中秋方才過去,月剛露頭而夕陽的餘輝閃爍的時候,吳錦翔吸著菸,「矇矓之間,想起了遣送歸鄉之前在集中營裡的南方的夕靄。自這桃紅的夕靄中,又無端地使他想起中國的七層寶塔。於是他又看見了地圖上的中國了」,他無助頹然,原先被「樂觀、情熱」壓抑得妥妥當當的戰時記憶,無可遏抑浮動了。
我們還沒看到吳錦翔毅然決然投入新的改革之中,也沒見到他的新的改革是什麼。但區分上述層次可見,當吳錦翔確認了祖國還在戰爭中,而可能還得持續一段時期戰爭的現實後,他的革命徬徨面臨更多必要調整。然而新的調整完成前,吳錦翔遭遇了另一件事,使他迅速落入萎縮及死亡。
1950年:現實再次來痛擊
吳錦翔深感無力,立即進入小說第四段。年過三十而逐漸墮落了,不再苦讀,只行些基本的教師道德。據說,墮落的吳錦翔的行為:
畢竟不只是一種道德或良心而已;而是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
單從吳錦翔自身,上述文脈依然容易證實為吳錦翔只不過是個無能的、改革不徹底,而空想的「市鎮小知識分子(陳映真)」。然而,小說家既然已經隱匿地通過吳錦翔批評了某一種改革論,則吳錦翔由「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意味著什麼呢?
這和「年過三十」當然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是與三十歲的標誌有關-1950年。1947年4月接下山村小學的吳錦翔是26歲,「年過30歲」當然就是小說家欲言不言,而使情節過分跳躍的時代背景。根據小說家後來在〈後街〉敘述的吳錦翔元形象也可以知道是白色恐怖:
那年秋天,一個從南洋而中國戰場復員、因肺結核而老是青蒼著臉、在五年級時為了班上一個佃農的兒子摔過他一記耳光的吳老師,在半夜裡被軍用吉普車帶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髮母親,一個人幽幽地在陰暗的土屋中哭泣。
語意不清的小說敘事,證實陳映真至晚在1960年便有這種認識:1950年代白色恐怖對於知識、現實改革等之可能性皆影響甚劇。對照史實與陳映真的記憶,吳錦翔實為活過了,或者說躲過了1950年代的肅殺的人,但「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的觸角」後震盪了的吳錦翔思維狀態,又一次受到搖晃。因著白色恐怖鋪天蓋地,墮落了的吳錦翔開始喝酒,「沒有什麼酒癖,但偶爾也會叫人莫名其妙地醉着著哭起來,像小兒一般」。吳錦翔曾經以為不再可能的「官憲的壓迫」又成為現實,吳錦翔應當感覺性命在懸。吳錦翔前兩年因為思想震盪而確認過了的戰爭現實性也果然持續,於是我們看到,先是壓抑、時而復甦的吳錦翔的戰爭記憶,在吳錦翔的學生的入營席筵上止不住地爆發。現實與記憶反覆疊合:
鑼鼓的聲音逐漸遠去,但那銅鑼的聲音仍舊震到人心裡面。太陽燃燒著山坡;燃燒著金黃耀眼的稻田;燃燒著紅磚的新農家。山坡的稜線上的樹影,在正午的暑氣中寂靜地站著。突然間,他彷彿又回到熱帶的南方,回到那裡的太陽,回到婆娑如鬼魅的樹以及砲火的聲音裡。鑼鼓的聲音逐漸遠去,砲火的聲音逐漸遠去。他傾聽著雨打一般的脆鼓聲,頃刻之間,又想起了在飯盒裡躍動的心肌打在盒蓋盒壁的聲音來。他擦著一臉一身的汗,有些詫異於自己的這個突然的虛弱和眩暈了。
此後,吳錦翔不斷虛弱,「南方的記憶;袍澤的血和屍體,以及心肌的叮叮咚咚的聲音,不住地在他的幻覺中盤旋起來,而且越來越尖銳了」。不到兩個半月,根福嫂發現他的兒子竟割腕自殺,死在床上。
小說第三節尾的徬徨,加之1950年後「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毀」,爾後是酒醉暴露的恐怖及誇張化的死亡,使本篇小說具有強烈的現實╱歷史批判意味。今日重讀,〈鄉村的教師〉鮮明批判國民黨集團階級性,且突出抗議「白色恐怖」。然而,急轉直下的1949年至1950年,卻讀起來有些漏洞。吳錦翔沒有被捕,雖無證據顯示吳錦翔是地下黨,也沒故事跡象指出他在戰後與左派保有任何聯繫,也沒有任何地下黨員逃來山村躲避的線索(雖然,吳錦翔所在的村,與陳映真三十年後所寫〈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的「大湖」同名,而大湖是地下黨被破壞後組織成員躲避地之一),而吳錦翔戰前一道「讀書」的朋友們也不見了。我們也可以說「過了三十歲的改革者吳錦翔墮落了」已濃縮隱喻了其他背景,但小說設定上的空白,也往往使讀者過度聚焦於「大的理想大的志願」,止於以「崩毀」乙詞設想其批判所指。然而我們實際上沒有讀到思想調整後的吳錦翔改革╱革命的具體設想,那麼,除了指認小說的現實批評、歷史化批評,又如何確認陳映真自己的「理想」與「志願」?
吳錦翔「大理想大志願」的困窘
我們見到吳錦翔回來台灣以後的心路轉折,他的樂觀與情熱,他的幻滅與質疑,並由於歷史上的事實而失去了持續實踐其改革者理想的可能性,終於墮落和不可遏抑的死亡。
吳錦翔剛剛回來時,確實質疑「知識或者理想在那個定命的戰爭、爆破、死屍和強暴中成了什麼呢?」從而,回到和平而樸拙的山村彷彿帶給他一些理念契機。但在樂觀與情熱中,吳錦翔即使懷抱熱情、(知識)信仰,卻自始無能為力。
由於讀書,且由於自己「出身貧苦的佃農」,使吳錦翔帶著某一種階級思想。小說家曖昧地說,「對於這些勞力者,他有著深的感情和親切的同情」,對農民的愛不是單純的愛,而是帶著「尊敬」。吳錦翔的理念誠然巨大,他覺得「務要使這一代建立一種關乎自己、關乎社會的意識,他曾熱烈地這樣想過;務要使他們做一個公正、執拗而有良心的人,由他們自己來擔負起改革自己鄉土的責任(後來改版為:務要使這一代建立一種關乎自己,關乎社會的意識,他曾熱烈地這樣想過:務要使他們對自己負起改造的責任)」,但同時,雖然吳錦翔「因為讀書」而有各種思想調整可能性,卻怎麼也無法調動學生的思想:
然而此刻,在這一羣瞪着死板的眼睛的無生氣的學童之前,他感到無法用他們的語言說明他的善意和誠懇了。他用手勢,幾度用舌頭潤着嘴唇,去找尋適當的比喻和詞句。他甚至走下講台,溫和地同他們談話,他的眼睛燃燒着,然而學童們依舊是侷促而且無生氣的。
吳錦翔回來後的山村,「村人」一直呈現為近似小說布景。但「一任坡上的太陽烘烤著褐黑色的背脊的農民們」,那些農家「破敗但仍不失其生命」,吳錦翔卻無法應對這厚重的、戰前與戰後不曾劇烈變動的社會內裡,無法鼓動「生」之契機。
吳錦翔追求改革但找不到方式把自己的「讀書」轉成「教讀書」,換言之理想與現實不能接軌。小說家沒寫第一次思想震盪後如何具體調整空想的「不完全改革」,且第二次思想震盪後,吳錦翔是步入墮落而不是再次調整,可見陳映真並未藉由吳錦翔傳達一符合社會現實的理想施展。革命徬徨令人悲愴,但吳錦翔的空洞無力復無力,本身不完整構成小說家自身「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如此就讓我們把視野放回理應是革命主體的背景-群眾,以辨識陳映真的思想。
太陽依舊炙人,生活依舊勞苦
村人們在光復後古鑼喧囂中熱心地歡聚著,在林厝的廣場,著實地演過兩天的社戲。但這薄薄的熱鬧與興奮,只不過是村人們對於戰爭死失的談論的暫時替代物罷了。征人未歸,幻滅「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悲哀」。村人們的熱心討論中,「我們健次是無望的了」、「後來留在巴丹的,都全被殲滅了!」也沒有過多憐惜的意味。戰爭、死屍、光復…只是村人農閒的傳奇話題,偶而騷動著卻不改變「宿命的、無趣味的生活」:
人們一度又一度地反覆著這個戰爭直接留在這個小小的山村的故事,懶散地談著五個不歸的男子,當然也包括吳錦翔在內的了。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那一年死去。或許這就是村人們對於這個死亡冷漠的原因罷。然則,附帶地,他們也聽到許多關於那麼一個遙遠遙遠的熱帶地的南方的事:那裡的戰爭、那裡的硝煙、那裡的海岸、太陽、森林和瘧疾。這種異鄉的神祕,甚至於征人之葬身於斯的事實,都似乎毫無損於他們的新奇的。
吳錦翔的母親毋寧也同屬這群形如魯迅式「看客」的村人。吳錦翔的母親,她誠然是開心的,而且開朗了、健碩了,她並且也是勞苦的辛勤佃農。由於母親的欲望,吳錦翔的母親執拗地繼續租種著一塊方寸的小園地,每日清早便去趕集,滿心想著養活兒子-教書無法自活。但吳錦翔的母親,卻也藉著吳錦翔,這位順從、沉靜、以苦讀聞於山村、被鄉人舉到山村小學裡任教的體面的兒子,而不停說嘴:
一向善於搬弄的根福嫂,便到處技巧地在眾人前提起她戰爭歸來的兒子。一等大家少不得要稱讚他的順從、他的教師的職位的時候,她便又愛著而且貶抑地自謙起來。
小說家反覆描寫山村的荒唐,逼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樣貌。到吳錦翔死後,讀者仍能看見那種於今不能說漸漸稀少了的,雜和著報與外人知的意味的「山歌一般的哭聲」。在傳統習俗裡,每一家死了人總得嚎哭數日,我們卻讀到,吳錦翔死亡當日,鄰家的年輕人居然有些慍怒於這樣一個不能說不常見的陰氣的死和哭聲,而鄰家的老年人頂多懶惰地嚼嚼嘴。
正是在這個節奏滯重的山村,吳錦翔感覺「窗外的梯田上的農民,便頓時和中國的幽古連接起來,帶著中國人的另一種筆觸,在陽光中勞動著,生活著」;也在這個本身即「中國式」愚而不安的他自己的村子,吳錦翔無法讓自己的思想調整與外在產生適當的勾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