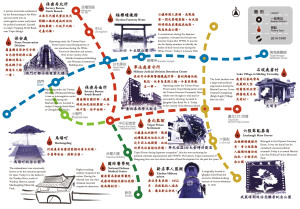♦文/吳澍培
我的名字叫做吳澍培,於1932年9月6日出生於台灣台中州北斗郡大城庄〈現在台灣省彰化縣大城鄉〉。大城的地理位置在台灣中部,西臨台灣海峽,南面濁水溪,是彰化縣最西南的小鄉村,多以耕農為主,由於土壤含沙率甚高,是個貧瘠的農村,農民都相當的窮困。
我的家庭在此偏僻貧瘠的鄉村裡算是中上的家庭。我家大概持有將近10甲的土地,父親就職於當地農會,所以大多的土地都放租於佃農,因此是個小地主的家庭。
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父親叫做吳瀛士,幼年念了些漢學(日據時期學習中國文詩詞史書等稱為漢學),11歲才到二林公學校就讀,因為當時大城還沒有學校。二林公學校畢業後進入台中第一中學就讀,畢業後在台中圖書館就職,一段時間後便回到家鄉在大城的信用組合就職,後來信用組合與農會合併成為農會信用部,一直到我被捕入獄後,才辭職不做事。1987年以86歲高齡終其一生。
我的父親由於幼時學過漢學,後來又跟吳家祖輩吳萬益一起回到福建同安尋根祭祖,所以民族意識相當強烈,不但不受日本人之利誘脅迫,始終不願改成日本姓名,也不願成為只說日本話而不講台灣話的所謂「國語家庭」,更常向我們兒女輩提示,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
然而,父親雖然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但亦有讀書人、小地主階級常有的清高、傲慢、閒逸、怕事等性格。例如,他曾與我舅父蕭玉衡參加「文樵詩社」,吟詩題詞等,後來在日本人的高壓之下,很快地就退出了詩社;又如,在我父親的朋友裡有人參加過反日的社會運動,如我舅父蕭玉衡、李應章、劉崧甫、張深切、張信義等,但是始終不曾看到我父親參與的紀錄,這可能與我父親懦弱怕事的性格有關。
我的母親叫做蕭嬌美,在幼年時讀過私塾(漢文),認得幾個字,尚能懂得簡單的文章。母親沒有正式進過學校讀書,一生相夫教子持家顧內,是個典型的家庭婦女,是老一代的人物,但也有鼓勵兒女讀書求上進的開放思想。在我被捕入獄後,我父親整個人將要精神崩潰的情況下,我母親反而能堅強的成為家庭裡精神中心,她至1997年以95歲的高壽逝世。
我是在上述的家庭背景下出生的,排行老二,上有大哥溫培,下有三弟澧培、四弟渥培及小妹季珍。大哥與四弟在家鄉,一個在開西藥房,一個從事幼稚園教育,三弟與小妹都到美國留學,都定居在美國。
民族意識的覺醒
我的童年是在家境不錯而純樸的鄉下長大,過的是無憂無慮的日子。上小學後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所以在我小小年紀時就有相當的優越感。但是,在我小學六年級時,台中州北斗郡在北斗日本神社舉行祭拜典禮及校際相撲比賽。因為我的體格不錯又擅長運動,所以被選為學校代表參加比賽。最後是大城公學校與秋津小學校爭奪冠軍。台灣人讀的是公學校,日本人讀的是小學校,秋津小學校在秋津村,是個日本人的移民村,全村的村民都是由日本移民而來的日本人。
相撲比賽的結果,我們大城公學校勝利了,但是日本裁判卻判秋津小學校勝利,並說台灣人怎麼可以贏日本人。我非常的氣憤並感到不平,大聲向裁判抗議並指責裁判不公平。然而得到的是幾個耳光及被罵「清國奴」(日本人常用此語罵台灣人)。我的優越感消失了,也不氣憤了,只得垂頭喪氣的掉眼淚,首次體會了被不同民族的日本人欺壓的感受。
小學畢業後,我考上台中第一中學,從鄉下走向城市,另一個環境。原本在鄉下我的家境是不錯的,到了城市後,我的優越感全沒了,反而感到有點自卑。在鄉下一般人都是打赤腳,我為了到台中讀書,家人特地幫我買了一雙鞋,日本話叫「它米」,是腳拇指與其他四指分開的膠底布鞋,多是腳伕與車伕所穿的鞋。我興高采烈地穿去上學,沒想到被同學嘲笑是「庄腳俗」〈鄉巴佬〉。當時雖然物質很缺乏,但是城裡的有錢人或從鄉下到都市來的大地主的子弟們,他們不是穿皮鞋,就是穿進口的布鞋。
受到這樣的刺激,讓我想起我在鄉下時,雖然沒有嘲笑過鄉下貧窮的小孩子們,但畢竟也沒有同情過,此時自己的尊嚴受損,就有強烈的不滿與不平。那些貧窮的小孩子們,不但是連上學讀書都不能,甚至連溫飽都不足,他們的不滿與不平應該會更強烈多倍。
台灣光復與二二八
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回到祖國懷抱了。台灣同胞不分男女老少,無不興高采烈的慶祝光復。我也參加了提燈籠慶祝遊行,很高興自己可以不必再做日本的次等國民,能做有尊嚴的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了。然而,高興的心情與對祖國的熱望很快地消失了,見到接收官員顢頇無能,到處廢產廢耕,物質缺乏,物價飛漲,民怨四起,我開始徬徨與不解。於是我努力學習國文,並透過書本雜誌去了解祖國的種種,還好,光復當初各種書籍雜誌相當豐富,於是開始膚淺地了解到弱國被欺凌的命運,積弱長久的祖國,自強不易。
1947年2月底,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發生的事件,消息很快地傳到了台中,3月1日在台中戲院舉行了群眾大會,我也在高年級學長的帶領下參加群眾大會。台上演講者都激昂地攻擊政府官員貪污腐敗,欺壓人民,百姓都生活在痛苦的深淵,呼籲大家團結起來和顢頇無能的貪官汙吏進行鬥爭。很快地就有群眾聚集起來,這邊一群,那邊一群的,去向政府機關抗爭。當時我年紀還小,所以沒有參加抗爭行列。
第二天,我與幾個同學由學長帶領到光復國校,那裡已有許多婦女,也有女學生在做飯糰,我們就搬運飯糰到群眾聚集的抗爭地點,給那些群眾吃。過了兩三天,我們學校宿舍裡的學生都陸續回家鄉去了,所以我也就離開學校回去家鄉,等到事件平息後,才又回到學校。回到學校後,宿舍裡大家交換訊息,熱烈討論。我除了學習語文外,對歷史、時事也格外關心,經常和同學一起討論。當時學校裡的風氣還十分自由開放。
加入共產黨
1947年9月,新學期開始了,在我們同房宿舍多了一位新同學,叫做彭沐興。他是高我兩屆的學長,從淡水中學轉學到我們學校來,很自然地他也會與我們討論各種事情。經過一段時間後,我發覺他的知識很豐富,見解也很獨特,於是我就經常請教於他,也常跟他討論得很開心,獲益不少。
1948年2月,學校放寒假時彭沐興邀我去他家玩。他家住苗栗縣銅鑼鄉。在他家住了兩三天,要回來時他拿了兩本書給我 ,一本社會發展史,一本哲學入門。他說,利用寒假看些書是很有益的。寒假過後我把書還給他,他便問我有何讀書心得?其實我很茫然,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心得。他便告訴我說,只要你能了解社會是發展的,社會發展的階段是從古代共產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進入人類理想的共產社會,並且也要知道社會發展的基礎是人類社會經濟物質生活的奮鬥結果,以後你就會有心得。至於哲學,是讓你能對事物認識的正確方法,以客觀存在為基礎,探討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的哲理,我還是不大懂。後來,他時常拿書或其他印刷品給我看,除了討論讀書心得外,也時常討論大陸國共戰爭的事情,以及近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社會等問題。
1948年10月,有一天彭沐興告訴我說,百多年來中國內憂外患不斷,國家積弱不振,自強不易,就是因為沒有能正確地領導人民,讓人民擁護的政黨。目前,只有共產黨才是唯一能使中國強盛,能讓人民安居樂業的希望。在大陸上,共產黨已經得到人民的擁護,對腐敗的國民黨進行致命的打擊,解放軍節節勝利,國民黨軍隊紛紛敗退。我是共產黨員,我看你平常學習認真,見解正確,又富有正義感,你是否願意參加共產黨?
這件事突如其來,我無法馬上給他答覆。經過一個禮拜的考慮,我認為要救國建國,更為了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中,應該要毅然答應。在我答覆他願意參加共產黨時,他就要我寫一份自傳,並要我取一個別名。於是我就自取「星光」為別名,寫了一份自傳交給他。
小組的第一個任務
1948年11月底,彭沐興帶來一位叫翁啟林的人來找我,說他也是我們的同志,以後我們三人就是一個小組,彭沐興為小組長,以後就一起學習,一起討論。翁啟林是高我兩屆的學長,也住在宿舍,跟我同室過,所以我認識他。
1949年1月底,放寒假之前的一個晚上9點多,有工作任務來了,彭沐興拿來一綑宣傳單要我們分頭去散發。除了我們小組三人之外,還有蔡茂宏和兩個我不認識的人。蔡茂宏也是我們學校的學長,我認識他。我們每人帶一部分宣傳單之外,還把一張電影院的電影說明書放在口袋裡,如果碰到狀況不對,就把宣傳單丟掉。假使被盤問時便說是去看電影,要回學校宿舍去。第一次的出任務,心裡有些緊張,還好那晚不到11點就順利完成,回到學校宿舍。
1949年3月初,彭沐興帶來一個叫江泰勇的,是台中商業學校的學生,他說你入黨的事已經通過,要我跟他去宣誓入黨。我就跟他到南台中的一家工廠裡的宿舍,由陳福添主持宣誓儀式。與我同時宣誓入黨的,還有蔡焜霖。蔡焜霖也是高我兩屆的學長,見過他,但他不住宿舍所以不熟。陳福添、江泰勇我都不認識。在回途路上江泰勇告訴我說,你現在已是候補黨員了。到了1949年5月,彭沐興又告訴我說你已經成為正式黨員了。此時我們的上級領導是李炳昆,我們開會時,他經常會來指導。
1949年6月底翁啟林畢業了。彭沐興因為休學了一個學期,所以變成春季班,還沒有畢業。於是我們小組就變成彭沐興、陳汝芳和我三個人。陳汝芳是我高我一屆的學長。1950年元月底彭沐興畢業了,我們小組變成陳汝芳、劉德慶和我三人。劉德慶是低我一屆的學弟,陳汝芳任小組長。
1950年2月,江泰勇來找我,告訴我說我們組織由台中市工作委員會改隸屬於台灣省學生工作委員會,由他當我們的上級領導,並要我在寒假期間到石岡的一個武裝基地受勞動訓練,於是帶我到石岡基地去一個禮拜,在山上種地瓜及搭草寮等工作。
被捕入獄
1950年3月下旬,蔡茂宏突然來告訴我翁啟林被捕了。蔡茂宏和翁啟林畢業後一起在一家電影公司就職。我感到事態嚴重,於是我就裝病向學校請假,並向房東謊稱要回鄉下養病(此時我已經不住在宿舍,在外面與幾個同學共同租房子住),不上學,亦不敢回住宿的地方,就到親戚朋友家住一兩天的東藏西躲,並注意學校與住處的動靜。這樣的過了半個月,因為沒有經驗及缺乏警覺心,認為一切很平靜,大概沒有事,於是就回到住處,準備又要去上學。
回去的第二天4月8日夜晚我就被捕了,同一晚上被捕的還有蔡茂宏及幾個我不認識的人。
半夜從台中被押同到台北保密局看守所,此處是在台北市延平南路,靠近小南門附近的一條小巷子裡,非常隱密的地方,又稱保密局南所。一進到牢房,我的心情非常惶恐,押房裡已有七八個人,往後要如何與這些陌生人相處,又想到偵訊時如何應對,陷入不解與無奈的心境。
在我心境困惑時,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楊春霖(張志忠),他在吃過飯後,大家在小房間裡走圈圈散步時,常會走在我後面,低聲地說小伙子在這裡要小心不要亂說話,把心情放輕鬆,日子會比較好過。有時會哼歌給我們聽。有兩條歌,我還記得很清楚,一條是日文的「紅旗之歌」、一條是「年青的朋友」,讓我的心情開朗了許多。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是林立,他是嘉義竹崎的醫生,雙腳因受刑求而紅腫得很厲害,睡他身邊的林坤西幫他處理傷痛。林立很喜歡下棋,楊春霖與林立似曾相識,下棋時會低聲地講一些我聽不到或聽不懂的話。
還有一位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許強,他是台大醫院內科主任醫師。他的性格好像很開朗,一進房內就說早知道會有今天,算了,不必煩惱。看到我們在下棋,就說下棋會使心情平靜,我喜歡和他們一起下棋。有一次他在跟我下棋時不忌諱地說,年輕小伙子你可能有機會活著出去,往後的人生自己好好地去把持,是對我的鼓舞。保密局是很嚴密的機關,許強的家人卻能幫他送過來日用品及食物,據他說他的病患與官方很熟。
後來張志忠、林立、許強都在軍法處被判死刑處決。(待續)